把文字交给漫天大雪——陈巨飞诗集《湖水》读后记
诗集《湖水》 陈巨飞 /著
(一)北方阳历三月方始,草木虽似乎已从冻僵中苏醒,却依然红翠了无。但是日子一到此时,它就被一种气息罩着,一场篾笼想返青的舒张,一次干枝低吟的苏醒,一种小马耳尖上竖起的渴望:想聆听,想触摸,想感知。恰逢此时,我收到了诗人陈巨飞的新诗集《湖水》,读之就是听闻“木浆哗哗,拨动湖水”,就是凝视“春风无言,吹拂往事”。(此两句出自陈巨飞的同名现代诗《湖水》)我倾心地捕捉一个异乡年轻人在我的心灵之水中所泛起的每一个涟漪,品味他的文字中情感与哲思的神韵,它们仿佛也都是我的,或者由诗行入目而变成了我的一般。我于是比窗外的春日先丰盈起来。
陈巨飞将属于他人生旅程中的生活细节、游历场景、与岁月的对话等转化和提升为与读者相通的情思脉动、心智灵光和精神意境,从而使他诗中的山水、花鸟、故乡、人物等“场景和物象以及回忆就不再单单是个体行为,而是具有精神共时体般的打通功能和历史化的共情效果”,(霍俊明语)让我不仅因看到诗人在自然中的徜徉、在生活中的前行、在往事中的追问而游目骋怀从而温习、反思和增加了生活体验与感悟,还让我从中验证了评论家敬文东说的话,“生活事件中早已本己地溶解了灵魂的各种要素,生活事件是灵魂诸要素、诸状态的形式;诗歌面向生活、研究生活,就是为了测度生活形式中的灵魂要素”,同时我感到也正是这种叩问让生活增值,让生命幻彩,让心灵丰盈深邃,从而发展人自身——沉思在诗歌中的意义突显出来了。是的,诗集《湖水》中,诗人的沉思细密、深邃且灵动、逸远,并且这沉思一方面是情感生动起来的沉思,一方面沉思使情感之焰的金边更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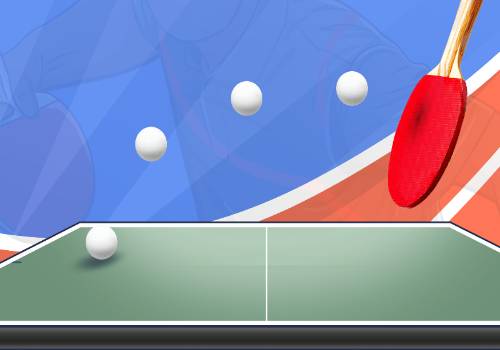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存在与时间
我有一只闹钟,它拒绝走动;
我有一颗核桃,它还年轻。
八岁时我参加过葬礼,
热闹的气氛让我也想跟着死一次。
我的穷亲戚,死时,
手里紧握一个废弃的钟摆。
她种过青菜的手,
现在攥着自己的时间。
她皱巴巴的核桃一样的脸,
是不再走动的钟表。
这首诗将对早亡的亲戚之思念与对存在和生死之哲思浑融一体。人间悲苦的体现与对终极问题的追问相碰撞,发出来的音响将为逝者所奏的哀乐又弹奏了一遍,悲伤在诗句语言的沉稳中如果因为哲思即理性之过滤而戴上了镇静的面罩,那么哲思是否能掩饰住那一层笼罩尘寰的哀痛?诗中的叙述语言的确将抒情压到低处,但是,那种与亲戚或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情感则是外溢的。整首诗起首两个“我有”把亲戚的遭际感同身受,与他者的躯体之隔被打破,对亲戚的哀痛就是对整个人类的哀痛——命运与死亡如剑悬在头颅之上并不太高的地方,婴孩也有握住钟摆之力,而谁能遏制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陨落。葬礼上的“热闹的气氛”是人的各种忙碌之一,而这带着“热闹气氛”之表象的忙碌充满人生,是青菜和皱巴巴的核桃一样具体的,抽象的存在与时间就在其中,谁能对之奥义绝对懵懂不觉?对那黑洞的凝望又将把心智视野开阔到什么样的境界,人间一游能因此在意义与价值之瀚海能多打捞几网收获?
诗人就是那个以有限生命追寻无限境界的精神漫游者,他在追寻生活意义的过程中,既找到光源又成为光源,他是生存的解读者,他给出的文本是诗性文本,包孕着语言的霓裳、情感的魅力、智慧的光亮,这样的诗歌如一条锦缎,比如陈巨飞的《湖水》《劈柴》《淠河志》《慢火车》等等。在《湖水》中,诗人临湖而感慨世界的多样性,春水涨与老树之老朽共时,而后者又令他想起亲人生命的枯萎,以及冥冥中是否有预报人间事的征兆。“向青草深处,寻找浩渺的老地方”是在点醒世人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是最终的皈依,那里有一个往事垒筑的城堡,就如胡弦在他的诗作《山林》中写的那样:“我们之所以未成为弃儿,正因为曾被一点点/放进经历过的事物中”。
《淠河志》里,陈巨飞启迪我往事或者是一条河,而人是往事的载体。“我不敢想象一条河在梦中站立起来,/幽暗的河水,会变成白色的瀑布。/我更不曾想,一个人静静地躺下来了,/变成一条无声的河流。”我相信思想的成果能给一颗思母之心以安慰:辛苦地参与淠河相关水利工程的母亲,最后以淠河为她在儿子心中长存的象征。这样,重读此诗第二节,我就对其情思内涵有了更多的领会:
我曾发誓要走得更远,比如:
到远方去,
到银河去,
到宇宙的未知里去。
可我从未走远。每当月明星稀
我都会听见,
淠河若有若无的流动声。
如此,在这首诗中,诗人在思与象通、意与境会、情景交融的独特“情境”下达到了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的领会和觉解。《劈柴》一诗亦然。兄长的“劈柴”是谢默斯·希尼之挖掘的另一种形式,他的“黑色的斧光/劈开了庞大的木质帝国”,劈开是打开境界、探问未知、通达妙理。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写道“他的汗水劈开视线/看见了被撕裂的两种生活——/他没有马可以喂,也不曾周游世界”。每个人都是有诗性的,虽然他不一定是诗人,哪一个人没有受到那“高空的光芒”的照耀,而谁又能挣脱俗世的庸常?王岳川所说:“当思想的羽翼触及道体的辉光,当骚动的灵魂潜沉到生命的内海时,诗人就于当下体悟中感领到永恒和无限”。所以,也许诗是实现灵魂返乡和诗意栖居的唯一途径与居所。
(二)以诗论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传统,比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赵翼的《论诗五首》等。臧棣说:“在古典传统中,它似乎是一种严肃的游戏。在诗人的生涯中,一个人何时会卷入这个游戏,原因很琐碎,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与诗人的抱负有关。”我认为《与同桌讨论非虚构》是陈巨飞的一首以诗论诗之作,而此诗中的诗句“相信我们在纸上的呈现”包含了他的诗歌抱负。
对于诗歌的虚构与非虚构古今中外很多诗人或者文论家都有过很多论述。霍俊明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诗歌的难度,意识到虚构和真实的难度。这关乎诗人对诗歌以及生活的态度。虚构是诗人的信仰,真实是诗歌的尺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他应该持有对于虚构和真实的双重热情。” 华莱士·史蒂文斯说:“最终的信仰是信仰一个虚构。你知道除了虚构之外别无他物。知道是一种虚构而你又心甘情愿地信仰它,这是何等微妙的真理。”
《与同桌讨论非虚构》中,诗人在第一节讲了虚实相生的问题。一方面,义理、思绪、情感等要通过物象来传达——立象以尽意,从而达到王夫之所说的“取景含情,但极微秀”,“杂用景物人情,总不使所思一见端绪”,不作“生人语”:上文讲到的《存在与时间》就是这样的一首诗。另一方面,写实要言外象外意味隽永,境界悠远:“群山吹起低缓的口琴,万壑有声”,从实物中生出幻象。在第二节里,诗人指出,诗歌要倾听奥义,要讲求表达方式,并且贴近生活、来自生活是诗歌真实性和生机的保证——“冒着热气”。主观真实是情感、审美与认知三位一体的综合结构,它是神秘的。这种主观真实“并不是单指内容的真实性,而是指它的内核是真实的。没有痛强说痛,没有愁强说愁,没有家国情怀强说家国情怀,说是非虚构,也可能只是保留了零散的事实,其出发点仍是虚构”。(百定安语)第三节诗句让我想起华莱士·史蒂文斯的一段话:
事实上,诗歌的世界是无法与我们生活的世界分开的,或者应该说,它与我们将要生活的世界无疑是分不开的,因为诗人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的形象,现在、过去或将来,都是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永远向往却并不了解的一个世界,是诗人赋予生活以最高虚构形式,舍此我们就无从领会它。
此诗中,“相信友人——他死于痼疾——在陀螺里/旋转。谁也救不了他”和《淠河志》中相信母亲“变成了一条无声的暗河”,都是“诗人赋予生活以最高的虚构形式”,它是慰藉、启迪、鼓舞和期盼。《雪饮》中“雪的独特性在于它的虚构”,雪“为河堤修复了伤口”等诗句呼应了《与同桌讨论非虚构》中诗人所持之诗观。
从这首诗的整体层面来说,为了更形象生动地表情达意,诗人运用了比拟手法,并且比拟不是局部的,而是贯穿首尾。如肖晓阳教授所说:“诗的表层义基于喻体,是虚构的。深层义则落到本体,是诗的主旨。这种表现手法可概括为‘言此意彼,虚实表里’,两个层面都必须意脉贯通。”《与同桌讨论非虚构》是一首非常耐品的诗作。《粉笔的造雪机》也是一首蕴含着对写诗之妙理慧思的阐发的诗作。“风,越来越具体,风景/变得抽象”是说诗要处理抽象与具体,有形与无形之间的转换、相伴和相生:比如粉笔与诗笔,造雪机与想象之间的隐喻等。从诗集《湖水》中的诗作里,我感到陈巨飞对诗歌艺术有着深入的思考、专研和实践。《雪中的乌桕树》写出了一个诗人对写作的一往情深:诗是他的热情也是他的燃烧,是他的美梦也是他的寻找,是他的此刻也是他的回望,是他在记忆中打捞也是他在当下创造:
雪中的乌桕树
新年落在旧雪上。风,是个动词。
钟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咳嗽,
住在楼下的人,内心
裹了一层蜡。深秋的一天,
他点燃过自己。而今,他从梦里
骤然醒来:一双脚印消失了――
像是悬念。天桥上,雪在聚集,
要把粉笔递给教书匠,要把
他的余生,递给一张白纸。如此
甚好。等他写完信,就将鹅毛
插进瓷瓶中。芜湖路是一封
长信,到了黄昏,路灯来读它――
此致,敬礼。记忆可以移植,
他记得过去的旷野,乌鸫一样的
标点符号,撒在成堆的云朵里。
他羡慕那些乌鸫、那些雪花,
他抖动毛茸茸的翅膀,致使词语
发生了雪崩……
(三)诗人是敏感的,自然界与生活中的各种光线、形态、运动,都能够被它纤毫不漏地捕捉到,他时刻做着这样的准备,并培养和锻炼着自己的这种能力。如果说这是入乎物,那么他也要能够出来,即用语言表达出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得惟妙惟肖,辞采飞扬:“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读陈巨飞《与同桌讨论非虚构》《雪饮》《粉笔的造雪机》《雪中的乌桕树》等诗作,我感到这几首诗中的雪可以象征他的神思飞扬纷纷,及其后继的想象驰骋、譬喻焕彩、哲理横生。
诗集《湖水》里,陈巨飞的游历山水之作中想象、譬喻的确使他的情感和哲思得到了很好的诗意的彰显。比如:“云在坡上骑马。雨,在水里绣花。/钻进伞中,微风一吹,/便成为延庆寺。/塔是斜的,天地间的偏差/却是最稳固的——传说没那么牢靠,/但经得起河流的冲击。”(《松阴溪逸事》)再比如诗人在花溪河畔的联想,借景抒情,表达了诗人怀乡、怀旧和对高远有神祇之物之念的仰望:“那时候,送信人翻身下马,/在花溪河畔,/将自己寄给一朵浮云。”“从前,野花分布为/神话般的体系。/鹅卵石也曾发光、飞翔,如果它是一粒陨石。”(《花溪河》)又比如《落雪的黄昏》中诗人借眼前景物联系和阐发人间事务的诗句:“雪落在野鸭身上,遮蔽了它的黑。/野鸭落在湖面上,/一个时间的破折号,呈现了/世界的扁平性。/路上的积雪有人清扫,湖面的积雪/却是合理的。”诗人观照自然,不是要停留在物质层面,格物最终是致知,像北宋理学家邵雍所说的:“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与同桌谈论非虚构》中,陈巨飞写道:“当我们把文字交给漫天大雪,/就像我们的交谈,/徒劳而深刻。雪化后,黎明开始拜访我们。”诗在俗常的判断中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但是它以其“深刻”照亮心灵,提升精神,帮助人抵抗平庸。
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陈巨飞善于将眼前现场的景观、事物转化为文学意义上的精神事件,将人们忽视的强化出来,使日常中被隐秘关系得以呈现。比如《小鹅花》中普通的花和普通的花间漫步的美丽、温馨和愉悦被凸显出来,使平凡的事物和生活反射出熠熠光泽。在《雪中的乌桕树》中,陈巨飞写道:“新年落在旧雪上。风,是个动词。/钟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咳嗽”。诗人时刻保持着警觉的观察和敏锐的感知,“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已逝之物和将来之物之间”(《松果收集者》),以一种生命之见的深度去测量另一种深度,呈现“原野的丰盈,果实的饱满”,“人世的幸福”和“经年的疼痛”。
陈巨飞“有飞翔和臆想的习惯”(《梦游者》)。他的诗是一个秘境:“当你进入/奏鸣曲,就会化为一个音符。”(《秘境》)他说用树叶拓片可以得到隐秘的星群。读他的诗,我一直希望我的手无限接近一枚“树叶拓片”。
- 把文字交给漫天大雪——陈巨飞诗集《湖水》读后记 2023-03-13 16:21:49
- 青年有话说:就业难题?从人才培养上“破题”! 2023-03-13 16:10:12
- 振兴乡村教育,首在教师 2023-03-13 16:03:10
- 全球即时看!一手房和二手房的区别 购买一手房的详细流程 2023-03-13 16:19:52
- 一手房和二手房的区别 购买一手房的详细流程 2023-03-13 16:20:17
- 2023年提前批有哪些学校 2023年提前批有哪些专业 2023-03-13 16:21:01
- 自考本科和统考本科有啥区别 自考注意事项 2023-03-13 16:03:55
- 当前快讯:2023年提前批有哪些学校 2023年提前批有哪些专业 2023-03-13 16:05:48
- 每日热文:自考本科和统考本科有啥区别 自考注意事项 2023-03-13 15:59:25
- 大四毕业体检可以不去吗 大学生毕业为什么要体检 2023-03-13 16:07:20
- 2023建筑设计专业大学排名全国 建筑设计专业就业前景 2023-03-13 16:07:56
- 注册会计师备考坚持不下去怎么办? 2023-03-13 16:16:30
- 焦点快报!大四毕业体检可以不去吗 大学生毕业为什么要体检 2023-03-13 16:16:44
- CPA题目这么多 怎么答题才能答得完? 2023-03-13 16:13:51
- 全球今日讯!备考CPA时间不够怎么办? 2023-03-13 16:16:55
- 全球今日讯!侯永斌指导:全年伴学考点30—最大诚信原则 2023-03-13 16:03:08
- 环球微速讯:榜样引领成长 三原中学举行初2022级表彰大会 2023-03-13 16:02:37
- 从生活中寻找春天的美!三岔湖初中举办教职工摄影比赛 2023-03-13 16:12:22
- 传承雷锋精神,万东路幼儿园萌娃在行动! 2023-03-13 16:18:14
- 万春镇中心幼儿园萌娃种下“‘植’属于你的春天” 2023-03-13 16:20:56
- 天天时讯:器以载德 非遗述廉 锦官驿小学廉洁文化进校园 2023-03-13 15:58:03
- 政通幼儿园大五班幼儿跟着家长认识人民币 2023-03-13 16:11:31
- 视讯!青羊区小学五年级数学教师齐聚金沙小学C区研讨课例 2023-03-13 16:11:38
- 注意!北京这些学校开设了国际艺术高中 2023-03-13 16:10:11
- 达川区石梯镇银铁中心学校召开2023年春季班主任工作会议 2023-03-13 16:06:45
- 焦点热文:幼儿误喝蚊香液后中毒变白肺 2023-03-13 16:01:01
- 热消息:深圳市东方学校招聘小学语文教师公告 2023-03-13 16:20:46
- 美丽中国·青春行动|西安培华学院师生开展植树节活动 2023-03-13 16:17:24
- 美丽中国·青春行动|西安培华学院师生开展植树节活动 2023-03-13 16:13:02
- 世界快看:西安翻译学院开展省级一流专业第三方评估 2023-03-13 15:57:15
- 最新资讯:西安翻译学院开展省级一流专业第三方评估 2023-03-13 16:00:02
- 历史性突破!长春中医药大学1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 2023-03-13 16:13:25
- 当前短讯!温泉小学多措并举做好宣传工作新篇章 2023-03-13 15:57:46
- 今热点:深圳龙华区诺德双语学校学费一年多少? 2023-03-13 16:09:34
- 全球报道:顺德文德学校A-LEVEL课程学费及简介 2023-03-13 16:09:19
- 2023年6月acca免考在哪查询?附查询流程 2023-03-13 16:10:50
- 当前关注:南通职业大学召开就业与创业工作推进会 2023-03-13 15:56:46
- 热资讯!2022年一造成绩哪天查 2023-03-13 15:48:40
- 世界热议:一级造价师证分数查询时间2022 2023-03-13 15:43:30
- 武汉:老年大学男模班大爷们走路带风 2023-03-13 16:04:21
- 速讯:关于公布2023年黑龙江省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计划的通知 2023-03-13 15:50:19
- 喜讯!郑州106高中学子绘画作品获佳绩 2023-03-13 15:58:45
- 全球微速讯:郑州11中邀请专家开展时政热点分析讲座 2023-03-13 15:39:59
- 热议:黑龙江2022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合格证书领取通知 2023-03-13 15:53:26
- 世界百事通!池州市2022年执业药师资格证书领取通知 2023-03-13 15:43:56
- 世界快资讯丨池州市2022年执业药师资格证书领取通知 2023-03-13 15:32:19
- 快播:淮南市2022年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办证通知 2023-03-13 15:37:35
- 黑龙江2022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合格证书领取通知 2023-03-13 15:36:09
- 甘肃2023年二级建造师报名时间:3月14日-20日 2023-03-13 15:39:51
- 信息:甘肃2023年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 2023-03-13 15:48:02
